

《雨》
文、图 / 廖博思
说起马华文学,你会想到什么呢?马华文学即是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发端于1919年,仅比中国新文学运动落后数年。可以说,马华文学是一种离散文学——从中国与中国文学离散到南洋,又在南洋的文化环境得以发展。多年的发展让马华文学渐渐有了属于自己的属性,地理和语言上的流动也为马华文学增添了其独特性。
今天介绍的,是马来西亚作家黄锦树的短篇小说集《雨》。《雨》是2017年台北国际书展大奖及金鼎奖文学图书奖得奖作品,同时也是 2018年首届北京大学王默人-周安仪世界华文文学奖获奖作品。
初读《雨》,你很难不被其中的南洋气息震撼:湿热的空气,阴沉的天色,仿佛永远也走不出去的胶林……这些意象反复连绵,极快地把你拉进了一个名叫南洋的异世界,这个南洋仿佛是你认识的南洋,又似乎不是——这里炎热、潮湿,大量的雨像瀑布那样倒下来,雷声爆炸,林间有蘑菇生长,有貘,有穿山甲,有石虎,有果子狸,还有飘荡的鬼火,和不为人知的巫医——这是一个作者心中的南洋。
《雨》注定是一部评论两极分化的作品。从结构上来看,它是一部短篇小说集,但从整体上来看,它也可以被作为一部长篇小说来读。全书共收录了十六篇作品,第一篇《雨天》是一首诗,此外十五篇是小说。其中八篇被编号,标记为《雨》作品一号、《雨》作品二号……而这八篇作品又不是连续的。其余诸篇如《归来》《W》等虽未编号,却都讲述同一家人的故事,主要的人物都是主人公辛、父亲阿土、母亲伊、妹妹阿叶,而所有发生的事也被不断下着的“雨”的意象穿插联结着,大雨小雨中,一切的事情失控地发展着:所有的大小故事都发生在大小雨里。老虎来了,日本人来了。女孩病死,男孩坠井死,妈妈心碎而死,父母被山老鼠抓到山林里……
黄锦树说,自己“借用绘画的做法把雨标记为一号,二号……八号,在小画幅的有限空间和有限元素内,做变奏、分岔、断裂与延续”,他是把“长篇的素材分散开去,让被叙述者与事件在不同时段存在,其后交叉混合”。
读《雨》的时候,我最大的感觉在于“变”,在书中,黄锦树构建了一个奇诡的世界,然后让主人公辛、父亲阿土、母亲伊、妹妹阿叶组成了一个外来下南洋的小家庭,依靠着马来半岛的胶林生活。在不同的篇章中,总有人在经历突如其来的失踪或离奇的死亡的厄运。但你也会发现,在下一篇章,他们又会“死而复生”……一时间,其实也很难明白,自己在上一章看到的是他们的分身?平行世界?抑或是梦中幻象?生离死别被不断的排列组合,人间喜悲在黄锦树的笔下何其轻巧:老虎把妹妹吃了,“都没有听到狗吠”;主人公辛掉入了煮食的锅中,“发现时两只脚挂在锅外,捞起来时,煮得最差的头,皮和头发一碰就掉了,手指也熟烂见骨”——生命如草芥,如沙,在《雨》的世界里,一切都是如烟如雾的幻觉与轮回。
在书中,有一个细节——故事的地点设置在马来西亚的雨林中,当地的华人都称自己是“唐山”来的——似乎海外(尤其东南亚)华人,都称自己的祖国为“唐山”,意为“大唐江山”——从中,我敏锐地感受到作者的乡愁。
这也许与作者黄锦树的经历有关。黄锦树祖籍福建南安,出生于马来西亚柔佛州。1986年到台湾大学中文系求学,并获得了淡江大学中文系硕士和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博士学位,1996年起任教于台湾暨南国际大学中文系。尽管已经在台湾生活超过30年,马来西亚依然是黄锦树小说素材的重要来源。和很多马来西亚家庭一样,黄锦树的祖辈在抗日战争前漂泊到南洋。他们在这个湿热的南国岛屿上做劳力,逐渐扎根,繁衍后代。
书里有一句话是这样的:“母亲说,你还是回来吧。故乡饿不死人的。”
这似乎是一句普通的描写,但当这句话出现在一本马华文学中的时候,这句话似乎有了更为广博的意义——这之中,“母亲”似乎不再只是一个简单的妇女,或许是他们的“唐山”,而故乡也不再是那片养大他们的雨林,而是祖国。
在小说中,似乎有很多这样那样流露出作者作为马来华人的身份认同的细节——
比如说,字里行间表现出的主角所在的华人家庭与马来人的隔阂,文化的差异和不认同,让他们互相疏远,彼此防备;又比如作者以报纸摘要形式罗列的,日军侵入马来西亚后对马来华人令人发指的罪行;还有二舅妈临死前一直在抄写的笔画残缺的金刚经,祖母对远在故国唐山的亲人的牵念,也随着同辈人的一一过世,变得无话可说,无人可诉了——这些偶尔露出端倪的信息,却铺展出雨林中若隐若现的深色背景,映现出那个时代南洋华人的窘迫、艰辛和灵魂深处的孤独。
小说中有一个小情节让我印象尤为深刻:几个革命人士劝一家人回国,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并且用这家人在战时“帮过日本鬼”作为谈判条件。革命人士苦苦规训他们“帮日本鬼是不对的”,但是父亲阿土只是淡淡反问“全家被杀掉才对吗?”
我们总是在各种作品中歌颂伟大英雄,但在雨林的这家避难者中,“自保”显得尤为真实,又尤为无奈。
华人也并非不爱国,他们为了躲避灾难在海外寻求“世外桃源”,换来的却是更加辛苦的工作——一切国内的人脉、关系、资产都已经被放弃了,同时还要忍受思乡的折磨。
热爱故乡,就要忍受折磨,忘记故乡,却又无法释怀“故乡”二字。
也许正像作者黄锦树在《雨》的后记中所说的那样:
“多年前离乡后开始写作,小说中即经常下着雨,胶林;常有归人,回不了家的人。”
“来自中国的旅人常说我们故乡的小镇肖似于中国南方的小镇。那南方,也就是我们祖先来自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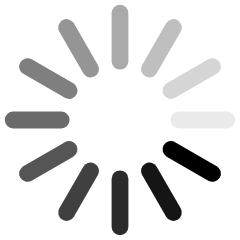 继续访问
继续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