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评《告别的年代》
文、图/廖博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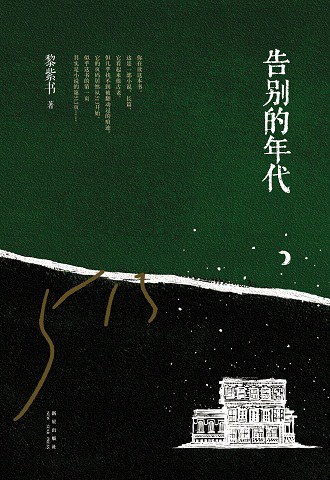
马华文学。
很奇怪,光是咀嚼这四个字,皮肤似乎便已经感受到一股闷热的湿气。
马华文学即是马来西亚华文文学。作为一种“小文学”,马华文学有一种“来自马华族群对华文文化存亡续绝的危机感”。也许正因如此,马华文学的创作总是难逃身份认同、国族焦虑、民族创伤、文明与野蛮的分野等母题。有评论家认为,马华文学背后象征着的是“身份认同”——大概再没有比马华作家更纠结的华人写作群体了:他们的先人从中国漂洋过海,现在却把离开马来西亚叫作“去国”,哪怕是移居大陆或台湾;他们是夹缝中生存的一批人,既得不到马来西亚主流文学圈的认可,又始终在大华语文学圈中处于边缘位置;他们拼了命地坚守中文,又早已不自觉放弃了先辈作家坚守的“故国情结”——侨乡亦是故乡、彼岸犹若此岸,马华文学一声声写出的,都是“乡关何处”的慨叹。
黎紫书曾说,“马来西亚华语文学,是战斗的、悲情的,也是多元的、温情的”,因为“我们从小就被教导去捍卫华人的一切权益,包括母语。我们比任何其他地方的华人都更抗拒失去什么,也更知道这必须用捍卫、抵抗的姿态才能保有”。
而她的代表作《告别的年代》也难以挣脱这种独特的“马华视角”。
黎紫书,本名林宝玲,1971出生于马来西亚的怡宝。1993年从霹雳女子中学毕业后即投入报界工作,作品由诗歌、散文再到小说,小说则有微型、短篇而至长篇。她的作品多次获奖,在马华作家中有“得奖专业户”之称,甚至被媒体称为“黎紫书现象”。
作为黎紫书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告别的年代》是令人惊艳的,正如她在开头中说的那样,这是“一本大书”,而且是一本结构“古怪”的“大书”,阅读起来,也许需要更多的耐心。
不知道有没有人像我一样曾经设想过这样一个场景:“我”在看电视,电视里的人也在看电视,而“我”之外也有人在看电视并进行点评——这部长篇理论上正是由这样的三层叙事来结构:“杜丽安”的故事,“你”的故事,作者与评论者的故事。三层叙事互为表里,彼此衍生与暗示,勾连出一部如同“书中书”一般的马来西亚华人的家族史。同为写作者,我首先关注的当然是这本书运用的技巧,而令我拜服的是,黎紫书在其中是真的肆意张扬地炫耀着自己独特的写作技巧。复杂的三层叙事中,时空变得交叠而扑朔迷离,在作者通过各种诸如打乱页码、虚构注释、仿造引文、运用大量暗晦隐喻的手段中,叙述变得不再可靠,历史和记忆交错互涉,每一层叙事都在相互质疑与提问,每一层叙事都在尝试自我拆解,整部文体逐渐复杂而精巧,仿如一把精致的万华镜——也许这正是作者本人想要表达的对于记忆与历史的态度——它们并非如历史书上写的那么确凿无疑;而是像这本《告别的年代》一样模棱两可,不但作者不明,甚至前后矛盾,彼此拆解,像两本不同版本的历史教材或在不同人口中对某一事件迥异的记忆。
这样独特而繁复的结构无疑也为本书添加了不少趣味性:你可以把这本书简单的归结为用“书中书”形式串联起的一个家族三代人的集体记忆,也可以因为作品反映了马来西亚华人的历史而将其作为管中窥豹的一个洞口,而在我看来更值得玩味的仍是黎紫书精巧的文本结构和由文学创作引出的虚实命题。
虚与实,真与假,一切都在文本中交错穿梭,谁是作者?谁是批评家?这到底是平行时空的故事抑或我们也是书中人?也许正如黎紫书在名为《想像中的想像之书》的后记中所言,“南洋已逐渐沉没在更浩瀚的时代之中”,当我们试图抓住记忆,试图书写历史时,我们会发现一切已变得暧昧不明,混沌难解。
我们总要与过去的年代告别,但拒绝遗忘,即使叙述已经变得不再可靠,记录中夹杂了大量虚构,但正如黎紫书在书中写的那样:“不要害怕去爱,爱只是个侏儒,却有高大的影子”。